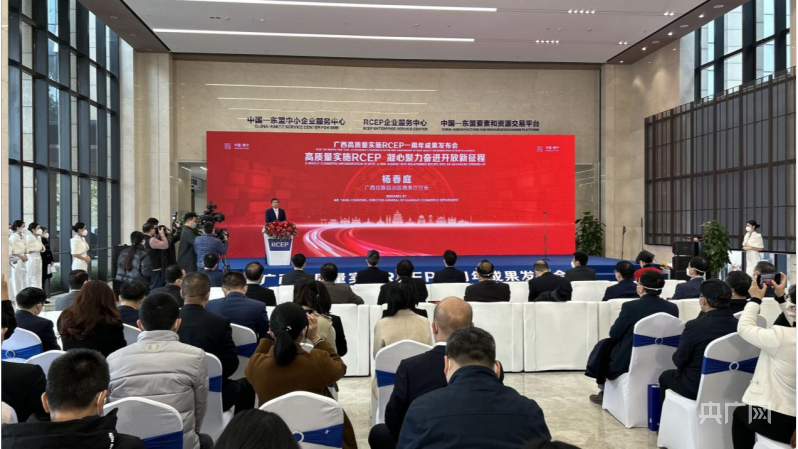生死 同居
2014-01-23 12:46:54 来源:东盟新闻周刊 导读:特约供稿:崔北河 无论新与旧,朴素和豪华,似乎无处不在的墓葬,屋顶都无例外地矗立一个十字架。伸向热带天空的十字架,醒目地昭示着

特约供稿:崔北河
踏上向往已久的苏门答腊岛几个小时后,就来到距棉兰175公里的火山湖多峇湖(Lake Toba),渡轮向湖中央的夏梦诗岛飞驰而去时,想起了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情景。伍尔芙的意识流名著《到灯塔去》,写一战后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亲密朋友去苏格兰某岛屿度假;欧大旭小说《和谐丝庄》,设计了一个“七女岛之行”。李有成教授认为,欧大旭采用康拉德式写法,将小说关键人物雪儿日记所记的七女岛蜜月变成了一趟热带森林的黑暗之旅。
可眼前漂浮在水面的Samosir Island,似乎是个如梦如诗的所在。
把Samosir Island写成“夏梦诗岛”,据说是台湾人的杰作,有徐志摩将Firenze译作“翡冷翠”之妙。
只在岛的边缘那些美丽度假村住几天,读书游泳休养生息,和抱着探索热带原始民族奥秘的欲望进入“岛心”,所获肯定不同。首先的意外是,岛上基督教堂随处可见。规模大些的教堂不说,似乎每几户人家,就会有个小教堂。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总人口的87%信奉回教,夏梦诗岛却是例外,50多个部落的原住民中,穆斯林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峇达人信奉基督。以整个东南亚历史来观照,这伴随西方殖民而来的现象不算突兀。但夏梦诗岛却又有着别处从未见过的一大景观:住宅式的墓葬紧贴着住宅,死者与生者同居。
和在海的另一边婆罗洲高原森林见过的“一条屋舍一个村,一扇门内一家人”的长屋不同,峇达人活着时住的是每家独立的船形长屋,死了也同样。一座座船型屋顶的墓葬散布稻田、湖畔、路边,更多的干脆就挨着生者的住宅——死者原先的家。死者那么贴近生者亲人,也贴近自己原本的生活。死亡,仿佛只是换到隔壁的另一栋房子去住。
从墓前插的木条来看,独立的墓葬为家庭共有。也见到颇讲究的墓葬群,同款式一栋栋船形屋比肩而立,安住家族先人。如同生者有贫富之别,墓房有简朴的亚答屋铁皮屋,也有豪华型双层石头水泥建筑。后者与活人住的房子一般体积并有精致的狮脸门神雕饰,栏杆整齐地围起花树繁茂的草地,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个富人的宅第。三四层的“楼房”也常见,有一种形状很特别:下面叠起两三层的高台阶,撑着顶端一个船形小屋,建筑的白墙勾出水蓝色线框,热带阳光下煞是鲜明。
后来看资料证实我没猜错,苏门答腊峇达人的一个习俗,就是人死后埋在住家旁边,不另辟墓地。所以有住宅、村庄的地方必有墓葬。当餐厅老板娘衣莎贝的丈夫驾车带我们奔驰在岛上,举起相机手机,无论拍远处的湖景,近处的村舍,不远不近的农田,画面里几乎都有清晰或模糊的墓葬的身影。
峇达人安顿死者的方式也在改变?途中见到300死者合葬的高塔式坟墓,应是较近期的了。但无论新与旧,朴素与豪华,似乎无处不在的墓葬,屋顶都无例外地矗立一个十字架。伸向热带天空的十字架,醒目地昭示着死者的身份:他们是信仰基督的峇达人!
我的手机拍下了一个很象征的画面:墓葬、住宅和教堂比邻而居——死者、生者与神同在。
虽然事先已了解,是美国和德国传教士改变了峇达人的传统信仰,但那日傍晚还是被震撼了。我们被带到一个须购票进入的“博物馆”,以前食人部落的古村。一排雕刻精美的高床式传统船形长屋前,是部落首领和长老们举行会议的石桌石椅,那些会议也包括审判战俘和罪犯的“司法会议”吧,几步之外就是刑场和石刀。博物馆的向导,一个黝黑健壮的中年男人绘声绘色表演部落祖先如何“千刀万剐”战俘和罪犯,如何饮其鲜血吞其眼睛及心脏,然后,显然已预见了我们的反应,他故意漫不经心地说,1814年,来岛上传教的第一个美国传教士,就被原住民“吃了”。
面面相觑,“花容失色”。
我知道在婆罗洲森林高原,是一个半世纪前建立砂拉越国的“白人拉者”詹姆士·布鲁克和继承人查尔斯·布鲁克,迫使土著达雅人改变了“猎人头”习俗。文献记载,布鲁克军队以火烧长屋、焚毁村庄,使村民因失去珍贵古物如头颅、古瓮和武器而极度恐惧的方法,教化土著放弃了“野蛮和残忍”。达雅人后来都跟随传教士成了天主的信徒。
那峇达人呢?无法想象,和东南亚许多原始民族一样信仰万物有灵,又至少延续了六七百年食人肉习俗的峇达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放弃了这一“传统”,被引导成为基督教徒,“走向文明”?
上一篇:“自由”的辐射
下一篇:滇池相会 圆梦中华 ——第三次世界越南华侨华人联谊大会